十岁的时候,我们的妈妈五十岁。我们是怎么谈她们的?
我和家萱在一个浴足馆按摩,并排懒坐,有一句每一句地闲聊。一面落地大窗,外面看不进来,我们却可以把过路的人看个清楚。
这是上海,这是衡山路。每一个亚洲城市都曾经有过这么一条路——餐厅特别时髦,酒吧特别昂贵,时装店冷气极强,灯光特别亮,墙上的海报一定有英文或法文写的“米兰”或“巴黎”。最突出的是走在街上的女郎,不管是露着白皙的腿还是纤细的腰,不管是小男生样的短发配牛仔裤还是随风飘起的长发配透明的丝巾,一颦一笑之间都辐射着美的自觉。每一个经过这面大窗的女郎,即使是独自一人,都带着一种演出的神情和姿态,美美地走过。她们在爱恋自己的青春。
家萱说,我记得啊,我妈管我管得烦死了,从我上小学开始,她就怕我出门被强奸,到了二十岁了还不准我超过十二点回家,每次晚回来她都一定要等门,然后也不开口说话,就是要让你“良心发现,自觉惭愧”。我妈简直就是个道德警察。
我说,我也记得啊,我妈给我的印象最深的就是她的“放肆”。那时在美国电影看见演“母亲”的说话细声细气的,浑身是优雅“教养”。我想,我妈也是杭州的绸缎庄大小姐,怎么这么“豪气”啊?当然,逃难,还生四个小孩,管小孩吃喝拉撒睡的日子,人怎么细得起来?她说话声音大,和邻居们讲到高兴时,会笑得惊天动地。她不怒则已,一怒而开骂时,正义凛然,轰轰烈烈,被骂的人只能抱头逃窜。
现在,我们自己五十多岁了,妈妈们成了八十多岁的“老媪”。
“你妈会时光错乱吗?”她问。
会啊,我说,譬如又一次带她到乡下看风景,她很兴奋,一路上说个不停:“这条路走下去转个弯就是我家的地。”或者说:“你看你看,那个山头我常去收租,就是那里。”我就对她说:“妈,这里你没来过啦。”她就开骂了:“乱讲,我就住这里,我家就在那山谷里,那里还有条河,叫新安江。”
我才明白,这一片台湾的美丽山林,仿佛浙江,使她忽然时光转换回到了自己的童年。她的眼睛发光,孩子似的指着车窗外:“佃农在我家地上种了很多杨梅、桃子,我爸爸让我去收租,佃农都对我很好,给我一大堆果子带走,我还爬很高的树呢。”
“你今年几岁,妈?”我轻声问她。
她眼神茫然,想了好一会儿,然后很小声地说:“我……我妈呢?我要找我妈。”
家萱的母亲住在北京一家安养院里。“开始的时候,她老说有人打她,剃她头发,听得我糊涂——这个赡养院很有品质,怎么会有人打她?”家萱的表情有些忧郁,“后来我才明白,原来她回到了‘文革时期’。年轻的时候,她是厂里的出纳,被拖出去打,让她洗厕所,把她剃成阴阳头——总之,就是对人极尽的侮辱。”
在你最衰弱的时候,却回到了最暴力、最恐怖的世界——我看着沉默的家萱,“那……你怎么办?”
她说:“想了好久,后来想出了一个办法。我自己写了个证明书,就写‘某某人工作努力,态度良好,爱国爱党,是本厂优良职工,已经被平反,恢复一切待遇。’然后还刻了一个好大的章,叫什么什么委员会,盖在证明书上。告诉看护说,妈妈一说有人打她,就把这证明书拿出来给她看。”
我不禁失笑,怎么我们这些五十岁的女人都在做一样的事情啊。我妈每天都在数她钱包里的钞票,每天都边数边说“我没钱,哪里去了?”我们跟她解释说她的钱在银行里,她就用那种怀疑的眼光盯着你看,然后还是时时刻刻紧抓着钱包,焦虑万分,怎么办?我于是打了一个“银行证明”:“兹证明某某女士在本行存有五百万元整”,然后下面盖个方方正正的章,红色的,正的反的连盖好几个,看起来很衙门,很威风。我交代印佣:“她一提到钱,你就把这证明拿出来让她看。”我把好几副老花眼镜也备妥,跟“银行证明”一起放在她床头抽屉。钱包,塞在她枕头底下。
按摩完了,家萱和我的“妈妈手记”技术交换也差不多了。落地窗前突然又出现了一个年轻的女郎,宽阔飘逸的丝绸裤裙,小背心露背露肩又露腰,一副水灵灵的妖娇模样;她的手指一直绕着自己的发丝,带给别人看的浅浅的笑,款款行走。
从哪里来,往哪里去,心中渐渐有一分明白,如月光泄地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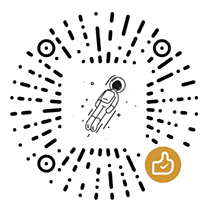
 赣ICP备2021001387号
赣ICP备2021001387号 粤公网安备44030002002531号
粤公网安备44030002002531号